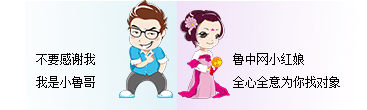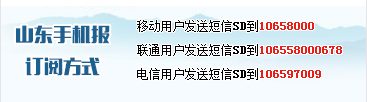我生活中的“三转一响”
2021-03-05 10:17:02
(作者 秦晓楼)
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知道,“三转一响”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它是那个时代的农村人对美好生活和幸福婚姻的四大物质追求。这四大件曾让极少数拥有者倍感满足和荣耀,又让大多数没有者万分羡慕、渴望和梦寐以求。
就“三转一响”而言,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羡慕、渴望和梦寐以求中度过的。
我出生在潍坊市昌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三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没上过学。那时候,有不少孩子多的家庭在春季青黄不接闹饥荒时靠挖野菜维持生活。我家虽没有缺粮断顿忍饥挨饿,但对“三转一响”那也是想都不敢想的。


一
我第一次见到收音机与我本村的六叔有关。
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六叔是另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员,他们经常在一起放牛,又加上有一点远房亲戚关系,故二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六叔的父亲早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带着六叔的三个哥哥去了台湾,排行四五六的弟兄三个留在了家里。许是因为这个问题?六叔四十岁了也没有找上对象成个家。他兄弟三个并不生活在一起,都是各自单过。到了晚上,六叔一个人在家孤独寂寞时间难熬,就常到我家和我父母在昏暗的油灯下抽烟拉呱消磨时光,我因此也和六叔混的十分亲近。
他一个整劳力,没有任何负担,故年终总能从生产队里分得八九十元的结余。六叔骨子里不是一个守旧落后的人,而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时尚的人。他养花弄草、喜鱼爱鸟,更崇尚现代文明。他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我村第一块巴掌大小的收音机。晚上,他到我家耍时,常常带着他的半导体,我喜欢的不得了。他们大人坐在床边炕沿上说话,我就躺在炕上饶有兴趣地拨弄这能说会唱的新鲜玩意。我很好奇——是谁在说话?难道里面有人?强烈的猎奇心理曾让我不止一次地打开收音机后盖查看。打开——盖上——再打开——再盖上,反反复复的探究,其浓厚的兴趣应该是源于年幼的无知和无邪的天真。
我家的第一块收音机,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花120元从南定百货大楼买的。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34.5元,为了买它,足足用了我大半年的积蓄。在家境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我仍然“不顾一切”地买了它,也是因为没有管住自己那颗骚动又没数的心。
我买的这块收音机已经不是单纯的收音机了,它同时还具有磁带录放功能。过去的收音机和它相比,其收听效果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那超大的音量、清脆的音质,足足让我的神情飞扬了一两年。每逢节假日回老家,我都会把它带上。在我们那个收音机还不多见的山村,它曾经不止一次地嘹亮和清爽过我家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耳膜和心灵。
后来,随着双卡录音机的迅速兴起,我的这种单卡的“半头砖”也就悄悄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二
在我参加工作后的1986年以前,我家是没有自行车的,但是,我小学毕业时就已学会骑了。
我临朐县的舅舅家和安丘市的姨娘家距我家都在四十里路以上。我的表哥逢年过节来看我娘时,大都是骑自行车来。我的姑父是吃公家粮的,每次来我家也是骑自行车。我姐姐们找婆家时,对方来人都是骑的自行车而且还是好几辆,其中有些还是缠着彩色塑料带、系着鲜艳红绸子的崭新的自行车。看着家里来客人了,院子里停着自行车了,我也就无心出去玩了,目光和心思都聚焦到了院子里的自行车上,总想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把它推出去,到大街上或场院里遛一遛。每逢他们上了锁,也会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变着法子去把钥匙要来,推出去骑一骑。农村的路很不平,有时候在外面摔了、磕了、碰了,回家也会挨大人一顿熊,但下次还是会如此这般地照行不误。我就是这样,在偷偷摸摸、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中学会骑自行车的。
有一天,家里来人给我二姐提亲,我便主动请缨,骑着来人的自行车到西北岭的庄稼地里把正在给队里干活的二姐接回家。回来的路上,很虎很野地学着村书记骑车下坡时身上的的确凉褂子在身后随风飘舞的潇洒的样子,故意将自行车骑得飞快。可因为缺乏驾驶经验,在一急拐弯处不懂的提早刹车,以至冲出路面,栽倒在路边水沟的沙滩里。
因为骑自行车,我曾经吃过大苦头。那时我在距家八十里外的县城读高一,有一次家里给我的周转粮吃光了、钱也花没了。一时接续不上,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饿着、靠着。也算是急中生智吧,在饿得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一个远房姨家的表哥就在学校附近的矿山机械厂上班。他是合同制工人,老婆孩子都在农村,隔三差五地要回六十里外的家里下地干农活,他都是骑自行车往返赶班的。于是我决定趁他上班时间借他的自行车,骑着回家拿饭取钱——因为当时确已身无分文,连坐车都成了奢望。
没想到骑车回家的路会是那么艰难。刚上路时,还是满面春风、精神焕发,心想:八十里路,足可以过过好久没骑自行车的瘾了。可是因为前两天没吃饭,骑车走了不到一半的路就再也骑不动了,平路上稍有点慢坡就骑不上去,只能下来推行。到最后走也走不动了,只感觉腿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环顾四周,人地两生,举目无亲。两眼无助、内心无法的我,只好停下来坐在路边的地头休息。那时,已全然没有了刚上路时的神采。就这样蔫巴巴、迷茫茫地坐了好一会儿,忽然间我眼睛一亮:前面地里快要成熟的麦子不是可以吃吗?这样一想,我立即研起了“小钢磨”——用双手搓麦子吃。搓了一会,感觉身上有劲了,于是开始继续往前走。走了一段又没劲了,就再坐下来搓。这样,走一段,搓一会,再走一段,再搓一会,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家。
这一路,真正让我感受和体会到了“饥饿”、“无力”状态下艰难困苦的真正含义!
我第一次购买自行车,不是为自己买的,而是受六叔之托帮他买的。在老家人的心目中,只要是在外地城市工作,就会以为你神通广大,什么事都能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自行车属紧俏商品,市面上很难买到,尤其是名牌。六叔托我,我当然会尽心尽力。那时候在农村,但凡想买自行车的,都是买载重量大的大轮自行车。人们最喜爱的青岛大金鹿凭一般关系根本买不到。就连淄博出的千里马和沂蒙山区一个兵工厂生产的金象,也很难买到。我托了同学,同学托了舍友,舍友又托了他自己的同学,这才从临沂那个厂子买了辆金象牌的。那朋友很热心地说找机会搭便车把自行车捎给我,可过了半年也没有捎来,我很理解,因为他们那里向我们这里跑的长途货车几个月也不见得有一趟。
眼见六叔着急,我便决定利用暑假自己去那厂里骑。
那时的交通和通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长途车很少,电话也只是单位和邮电局里才有,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络主要还是靠书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仅凭“厂子在沂源”这一点并不确实的信息,就毅然上路了,这符合我当时年轻冒失的性格特点。
第一天,因为没赶上五十里路外的去沂源的客车,只好改道去了临朐县城。
第二天,从临朐县城赶到沂源县城,多方打听,没人知道这个厂子的地址。最后,还是从邮局了解到:此厂不在沂源而在蒙阴。
第三天,在去往蒙阴县城的长途车上,我边走边打听。在热心人士的指引下,我从一个叫岱崮的地方下了车,又步行十多里,终于在一个大山沟里找到了这个厂子和帮着买自行车的那个陌生朋友。
第四天,早晨六点,我在厂里吃了一顿工人常吃而农民少见的相当幸福的早餐——半斤油条、两碗豆浆,然后骑上崭新的金象轻松愉快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经过六个小时的翻山越岭,中午12点,我到达了沂源县城。为了防止太累,也是购买的新自行车到手后有了闲情逸致,我决定在沂源县城休息半天。下午,游览了县城南面的沂河,只见十分宽阔的河面上,横亘着不久前被洪水冲断的大桥。桥面上那一根根严重倾斜的拳头粗的铁栏杆,告诉了我洪水的凶猛与可怕。晚上,又在坐落于沂河边上的沂蒙新华制药厂看了一场露天电影,《小兵张嗄》中抗日将士那矫健的身影和清脆的枪声一直萦绕到了我熟睡的美梦里。
第五天,我仍然是六点出发,骑行8个小时,于下午两点到达了昌乐县漳河老家。进门后,我把自行车往院子里一插,那感觉那神情就像自己是从战场上归来的英雄。
小时候常听娘说:孩子对父母的心思只有筷子那么长,父母对孩子的心思却和脚下的路一样长。这比喻很形象也很恰当,一点也不假。孩子的心在外面的世界,父母的心在孩子的身上!到家后我才知道,病床上的父亲和满头白发的母亲,在这五天的时间里为我担了多大的心!
母亲对我说:我走的第二天,庄上的大喇叭里广播,在临朐县五井,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一穿白褂子的小青年身受重伤……他(她)们越听越像我,越想越不安,以致晚上整夜睡不着觉……人,有些记忆是留不住的,而有些记忆是抹不掉的。现在我能清楚地记起,当时我刚到家正在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开大门时,已经病得下不了炕、连话都无力多说的父亲,曾对着正在外间干活的母亲大喊过这样一句话:快去开门,孩子回来了!我进家后,看到父母喜悦得有些激动的表情,哪曾想到这几天他们在家过的是度日如年的日子——我这不孝的儿!
在由蒙阴返回的路上,所遇到的人,几乎看不到有骑自行车的,都是靠两条腿走着,有挑担子的,有背包袱的,骑行在他们身边嗖嗖而过的那种感觉,不亚于本世纪初买了私家车的人,驾车行驶在骑自行车的人流中。
路上给我印象最为清晰深刻的是,从沂源县城出发进入山区公路后不久,即遇上了暴风骤雨。白茫茫的雨幕中,蜿蜒曲折的山区公路上见不到一辆行驶的汽车,只有我顶风冒雨艰难前行。行进中,两耳充满了山洪的巨大轰鸣和野鸟的悲惨鸣叫声。独自骑行在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的山腰间,我居然一点都不感到害怕,反而有一种饱赏风雨中大山美景的兴奋和愉快。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深深地感叹:人的精神的力量真是无穷的!我想:我当时无惧无畏的精神支柱,除了年轻,大概也和载着我一路前行的崭新的金象有一定关系吧。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87年初购买的青岛小金鹿牌自行车,是用来带女朋友的。结婚后给媳妇买了一辆安阳三枪牌弯梁自行车,是用来比翼双飞的。孩子上初中后,我们又买了一辆广州五羊牌自行车,是用来供孩子上下学的。至今我们还完好的保留着女儿的车子,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家的重要印记。

三
孩子上学之前我家不曾有过闹钟,更不曾有过挂钟。我小时住舅舅家,夜里听着他家墙上那个老式挂钟发出浑厚悦耳的报点声,总能给人一种文雅、高贵的感觉。舅舅是公办教师,表哥是赤脚医生,在我的心目中,那时挂钟就好像是书香门第和大户人家的标配。
手表是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后才有的,是姐夫把自己带了多年而且颇为珍惜的钟山牌手表毫不犹豫的撸给了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后,还是姐夫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60多元为我购买了崭新的聊城牌手表,让我在手表上实现了第一次更新换代,而那块老旧的钟山手表又回到了姐夫的手腕上。想到这些,我心头忽然一阵感动,泪水顿时盈满了眼眶!
那时的钟山手表30元一块,与120元一块的上海牌手表相比,虽然档次不高,但确也经久耐用且计时准确。
我已多年不戴手表了。今年,为了我的生日,女儿静悄悄地给我买了一块浪琴高端间金手表。尽管现在的我已不习惯戴表了、更不想追求什么品牌,但这块手表我会戴着、一直戴着、直到老去——女儿有女儿的厚意、老爸有老爸的深情。
我是从不拿自己的生日当回事的,每年的生日我几乎不曾想起过。但女儿对我的生日,自她懂事起至今二十多年,却一次都不曾忘记过!

四
第一次见缝纫机,是在我本族一个大叔的家里。大叔是我国援建坦桑尼亚的汽车司机,每月两份工资的收入使他的家境很是殷实。他家的照相机、电视机和缝纫机大概都是我村的第一部。虽然家里有了缝纫机,大婶却不会用。它被摆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常年不曾有人动一动。看来它的存在也只是成了那时大叔家良好条件的一个象征。
我家的缝纫机是结婚时妻子的大哥陪送给妹妹的名牌——蝴蝶牌。她擅长裁缝,喜欢缝纫机,十分珍惜地用了很多年。我和孩子的许多衣服都是妻子亲手裁制的。我也正是从那时起,才彻底改变了穿衣服颜色、款式、肥瘦、长短常常被人笑话的窘迫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缝纫机的利用率越来越低,我身边的人,更多的是喜欢到40里外的淄川服装城或附近的百货大楼,购买既便宜又好看的时髦服装。我家的缝纫机也因此闲置在车库里被冷落了许多年。前年,差点被人100元买走。今年,因为车库要改做他用,又把它搬回了家里。安放到合适的位置后,一种分明的感觉忽然涌上心头:家里还是有个缝纫机好——它能使家更有家的样子,能使家人更真切地感受到家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