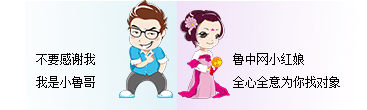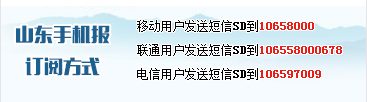《漫长的季节》如何穿透悬疑抵达人生?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23-05-12 10:06:39
◎韩思琪
时隔十几年,连接此时与彼时,在不同的时代里追缉同一个谜题故事,用横跨十余载甚至几十载的破案过程串起剧情,将人物的命运起伏镶嵌进时代流动的全景图中——如此编织剧情在今年格外流行,于是我们看到了《狂飙》《平原上的摩西》《他是谁》《尘封十三载》。主角们为自己心里的“执”,在各自的命运里被生活打磨、蹂躏、辜负,仍要提起“剩勇”去追“穷寇”。
近来“高开爆走”的《漫长的季节》亦是如此,豆瓣开分9.0,完结后升至9.4,难得的叫好也叫座。剧集完结后热度不减反增,想看与在看人数同步快速攀升。
《漫长的季节》何以封神呢?
真正打动人的,一定是“人”的故事
《漫长的季节》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剧集。以工业化成熟度为代表的创作,往往重剧情、看重故事性,用精巧的结构骨架去讲故事。而另一种作者性更强的创作,则多选择人物为先,看向更细腻的血肉塑造。
主演之一秦昊说:“悬疑是壳子,内核是人生。”诚如此,《漫长的季节》的重点首先是人物塑造,镜头紧跟着人物,构图、取景框、色彩全部服务于人的处境。而时代的切片,经由角色投射为一种纵深的思索,勾连起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脉搏。从时代的火车头上下来,是王响这类人一生的寓言。
无意拉踩,也不能说是要在二者之间划分一个高下。只是,在当下这个疯狂分心的短平快时代,《漫长的季节》选择的其实并不是一条具备国民度优势的路。因为所谓更适应于倍速时代观众耐性的国民度优势,往往依靠前面说的“故事性”,一如《狂飙》编织的大开大合、刀砍斧凿的剧情转折,精巧而爽利。
《漫长的季节》则选择以人为先,几乎所有的角色单拉出来都能够充当一部文艺作品的主角。这更像是经典文学的审美趣味,剧中人的“人设”都很难去概括——他们不扁平,每个角色都被赋予了丰腴的内核。
王响,典型的东北味儿“爹”
范伟出演的王响是《漫长的季节》的灵魂人物。1997年,他是意气风发的火车司机,开得了二十挂的钢铁巨兽,是桦钢连年的劳模。敬业、爱岗、正直,真正地把桦钢当作自己家。同时,他也有一些作为东北男人“典型范本”的缺点:偶有一些小的攀比和虚荣心(多次强调父亲是挖建厂第一铁锹土的元老,自己是“根正苗红”的钢厂接班人)、色厉内荏、对领导唯唯诺诺、对内有大家长式的权威。
儿子写诗被他发现,“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他马上会摆开“爹”的架势:“诗这玩意儿,讲究个合辙押韵,第一句,打个响指吧,第二句就应该是,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
你能看到他随时随地在进行的“价值圈地”,通过对儿子的否定来圈定他的话语权、定义权。但他的“爹”,不只讲权利,也讲义务,“责任”二字刻在了王响的血液里。所以当丧子、丧妻后,他想卧轨自杀,最后却被一声婴孩儿的啼哭唤醒,挣扎着活下去,去直面人生避无可避的痛苦。
在第11集,王响与龚彪、马队三人喝酒唱歌,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说“人生不如意者十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声色光影,笑中带泪,悲中带喜,意味深长。最终的结局,老年的王响与壮年的王响“相遇”,壮年王师傅豪迈中不知大厦将倾,老年王响反复叮嘱“向前看啊!别回头。”
龚彪,乐观的东北老舅
秦昊出演的彪子,人如其名,彪,坚定的人生如梦主义者。
作为上世纪90时代的大学生,他从前途敞亮的天之骄子到干啥啥不成的出租车司机,除了他性格里的不够靠谱,更是时代寓言的承受者。面对生活肉眼可见的步步坠落,“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龚彪接受了一切,“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他没有心结,活在当下,甚至有一种当下颇为推崇的“松弛感”,如同黄油化开一样。
龚彪就像东北最常见的娘家老舅,亲切、善良、穷大方,无所谓吃亏、不计较、出事时也愿意出头。同时,又有一点儿油嘴滑舌、插科打诨,没有什么坚挺的事业野心。成家后,坚定地不伸手帮一把家务,婚姻生活把自己心中的“朱砂痣”过成了“蚊子血”,一地鸡毛。
龚彪的故事线其实独立于主线外,但他的戏份是剧中的一抹亮色,作为王响和马队的对照项,他的乐观接住了观众,接住了陷入沉重灰暗往事中的观众。知命而不惧,最终中彩票与车祸接连的大起大落,让彪子的人生也停止在“如梦”的结局。
马德胜,跳拉丁舞的刑警队长
陈明昊出演的刑警队长——马队,是面对陈年旧案真相的第三种态度。他从未忘记,多年来仍挂念真相,只是出于纯粹的良心,要替被损害被侮辱的受害人讨一个公道。他不愿蝇营狗苟,将人命看得重于业绩。但是,也有着“大男子,小气量”的一面:他养了条狗,起名“小李”,为的是叫一叫过去自己的手下、现在的李局——“小李”。脑梗后回警局,他忘记了很多事,但仍记得自己是小李的领导,他的权力时刻,和他权威象征的暖壶。如此种种,反而让马队——这个会跳拉丁舞的刑警队长更加饱满、真实。
黄丽茹,有生命力的中年女性
难能可贵的是,《漫长的季节》并没有扁平化地处理女性角色。
丽茹是厂子里有名的美人,她爱美且自知,将美貌和性感作为自己的资源去使用。剧中最经典的对话发生在她和龚彪之间:在龚彪约她看电影时,龚彪炫耀着自己的学识。丽茹反问他:“弗洛伊德是谁啊?他分房了吗?”彪子讪讪地答,“那没有,他不是咱们厂的。”
她有点儿现实,在厂长和龚彪之间摇摆,有着生活的盘算和衡量。丽茹与彪子最终分道扬镳,是人生的现实至上主义者和浪漫至上主义者生活程序的不兼容。但也正是这样立体的塑造,让丽茹从贤妻良母、大男子主义家庭的“受害者”身份上松了松绑。
丽茹不需要完美,也不需要苦情,这二十年她为婚姻生活努力过,也一次次地失望过。爱是真的、失望也是,所以最终只能选择分手。从丽人变为医美失败、有着全包眼线唇线、吵起架来嗓门震天的中年妇女,不够完美的黄女士有着别样的生命力。
沈墨和殷红,残酷命运的对照组
沈墨和殷红,就像是对照组。她们因为一点儿相像而被港商误认,也开启了后面的悲剧种种。沈墨相关剧情的反转,也是开启《漫长的季节》“封神”路的第一个高潮——她不只是一个被损害的象征、一朵小白花,也是最终会反戈一击、用自己的所有去复仇的少女,会“要你知道,人和动物不一样”。
黑与红,浓稠、悲情。隔着彼此的人生,她们欲望着对方的人生:殷红想成为沈墨,想要摆脱母亲那般被劣质便宜煤气罐炸死的贫困人生,她羡慕沈默可以弹奏钢琴的“矜贵”,偏执地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弱和惨是她为自己的贪婪找到的通行证。而沈墨其实也羡慕殷红,比起寄人篱下被人侵犯,她宁愿选择与亲人一起相依为命,或许清贫但拥有自由,最后沈墨也“变成了”殷红。
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用细节铺满了他们的肌理,即便是一闪而过的一个小角色,如任素汐扮演的餐馆老板娘,那句此地无银的“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这些细节,就是是枝裕和提到过的“波动”,“附着在剧情主轴上的一部分情绪”。这些细节上的波动,是提供给观众“这情绪我理解”的代入接口。
东北往事,怎么从小众抵达大众?
文学标签化的东北
《漫长的季节》以一桩碎尸案为引子,用1997年、1998年与2016年相隔近20年的时空对照,徐徐揭开一段东北家庭的神秘往事。东北,尤其是文学标签化的东北,与悬疑罪案的融合,正成为一种国产悬疑故事的模板,《无证之罪》《胆小鬼》《平原上的摩西》《东北旧事》均在此列。
所谓文学标签化的东北,是“众所周知,东北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寒风萧瑟,形容时间停滞,形容猛虎入笼,形容望穿尽头”;是充满东北元素的符号——伫立的大型机器,工人下岗潮,破败的厂区,舞厅与洗浴中心,豹纹裤烫泡面头的阿姨,接天连地的大雪冰河;是一种暗调蒙板,“东北文学,总是带有时代大手不可置否的一扬,轻轻击碎无数个家庭的灰暗底色,雾蒙蒙的。”
从电影《钢的琴》《铁西区》,到近些年的东北文学、改编自这些小说的影视剧,一种更新的“东北伤痕文学”正在标签化着东北:颓废、破败、冷冽、粗粝的工业锈带上,生长出的带有质感与怀旧浪漫情绪的意象。诗歌、音乐、拉丁舞,被命运“撞倒”的人们承受着时代的句点。
飓变来临。东北下岗的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小家庭生活,体制内可接班的“铁饭碗”失效,厂区原本稳定生活的优越性与“确定性”的被取消。如此降调的故事,在时代巨轮猛进时还只是一种地方性的生活经验,虽被国产悬疑类型所偏爱,却似乎总难撬动更广泛的全民式共情。
穿透东北符号的“破”
《漫长的季节》能够穿透东北文学、东北影视的地域性经验,从小众抵达大众,源于一种“破”。
首先体现在突破东北刻板印象的影像语言。《漫长的季节》一改以往刻板印象的拍摄风格,被观众调侃说“想给辛爽颁发‘为中国悬疑剧开灯’奖”。与冷色调、工业感不同,导演辛爽在《漫长的季节》中对东北意象的取用,搭配了感性的、日常感的暖色调。
暖调日常流配以了东北的“仗义”叙事。东北人的仗义,带着一点侠气,不只存在于老年三人组的友情中;也存在于老年王响和邢科长的泯恩仇。看到邢科长挂着的尿袋,王响愿意为昔日的同事保住他所剩无几的、被昔日权力象征的大衣裹住的、最后的尊严与体面。这种“仗义”甚至还存在于龚彪对丽茹的爱情中——“没孩子就没孩子,大不了我们养点儿别的。”
这种“仗义”是不够市场经济的、不够理性的。在日益被新自由主义接管权责观念的亲密关系里,不会步步为营、不能“拎得清”,甚至是前现代的。但《漫长的季节》的精巧在于,辛爽不撕裂,剧情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既不煽情、不试图建构某种“情义”的价值,同时也不过分冷冽、去消解“仗义”的价值。尽管困在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伤口,被困在那个漫长的秋天,亟待重启人生。《漫长的季节》的剧情并未止于或沉迷于展示伤口,尽管被诟病带有一些“小品性”,但《漫长的季节》总是先抖了包袱再咂出一丝苦味,而不是靠“伤痕”去“绑架”观众的认同与眼泪。
心灵创伤的共同治愈
与其说《漫长的季节》的胜出是社会派推理的魅力,不如说是所谓生活流悬疑剧的一次有效“告解”。一如在搜索引擎里输入 how to forget,当输入到how to f-o-r-的时候,搜索器就会自动弹出how to forgive yourself,遗忘与原谅居然共享着同一个解法:放过自己。
至12集终章,图穷匕见,王响终于解开了儿子的死亡之谜。这一盘踞在他心头、萦绕在梦中20年的心结,他必须完成的事,他的憾恨。从过去来的雪落下,穿越了十几年的秋天,人们共同沐浴在同一片初雪下。
当然还有故事讲述的时代。共和国长子曾经如何、如今怎样,“静谧的城郊,废弃的矿坑,像一只巨大的碗,掉漆的铜雕和空荡的碗底是城市的落款。”当面对近乎家破人亡的命运,“王响们”又要如何处理这样重的伤?面对无法回避的痛苦,“当尘埃落下来时,普通人做到‘往前看’,就是对各自头顶大山的抵抗。”如此创伤性的经验,之于后疫情时代的人们来说,不可谓不是一种心灵创伤的共同治愈。
对于创作者来说,《漫长的季节》的启示录或许在于相信今天的观众,审美是在线的。创作者要做的仍然是那句——尊重观众。正如辛爽的95%理论:“观众是整个团队的最后一波儿主创,当我们都完成之后,作品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应该把它交出去。观众对剧情的讨论、解读,以及情感发散,最终才会形成一个作品最后的样子。不能以一种傲慢的姿态来创作,我们也不能站在一个制高点说观众就应该怎么样。”
对他来说,“如同每集的片尾曲,那一刻我和观众都没有在表达,但那种沉默不代表没有沟通,而是精神层面的共鸣。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去表达,文艺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让人产生联想。”
那么,就让我们也打个响指吧,打个共鸣的响指。